[付费阅读,自主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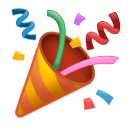


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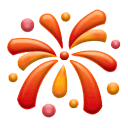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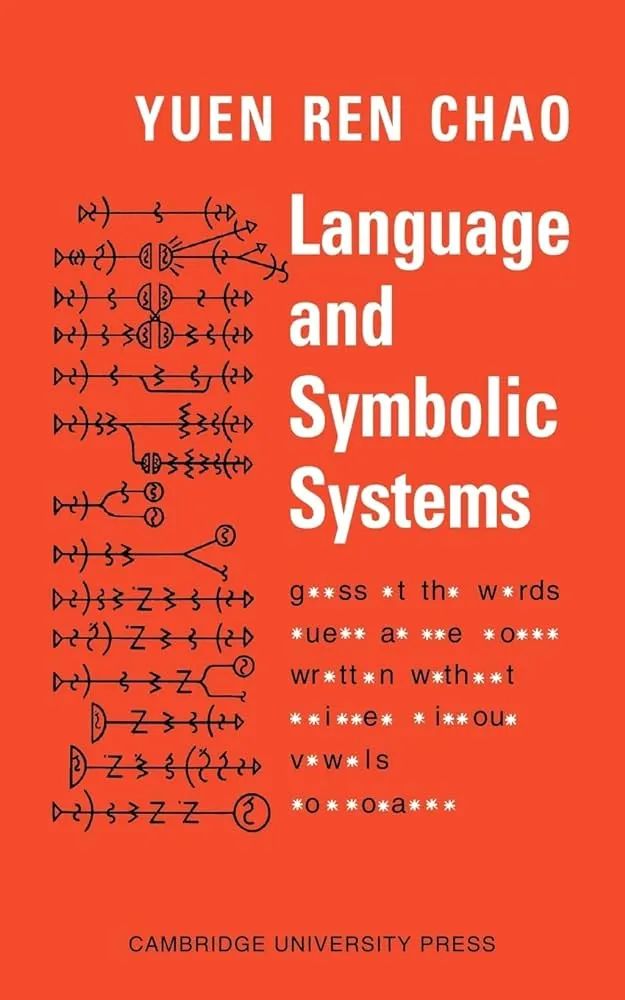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
1968年是赵元任先生的“出版年”,两部经典横空出世:一部是《汉语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的同时,另一部则是《语言与符号系统》(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赵先生说这本书是在《语言问题》的基础上“改编”的,但由于要“把对中国人须说须省的话跟对西洋人须说须省的话不同,所以内容有好些出入”(见“新版序”)。
在我们看来,此书可谓是赵先生语言学观的集大成体现,可作为理解《汉语口语语法》及所有其他著作的基础;而从教材的角都来考察,此书则可谓赵先生的“语言学纲要/概要/概论”,论及了语言与语言学的方方面面。纵观此书,再以其他类似书籍为参照,我们发现此书有这么几个特点:
〇词汇与语法的连续统观,体现了构式语法的观点;
〇关心语言之用或语言技术,如机器翻译、计算语言学(见第11章“语言技术”)
〇处处体现了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如信息科学)的交叉(比如赵先生在论及语言的统一和多样时,提到了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p. 123);
〇最后以“符号系统”结束全书,践行了索绪尔的呼吁,同时呼应了题目;
〇鲜明的个人特色,是基于研究(尤其是个人研究)“写”出来的,而非现如今很多类似书东拼西凑“编”出来的;
〇该书因为时代因素有缺项(如“语音感知心理学”“语用学”),但是赵元任心中有一个很好的轮廓或框架,值得后人继续填充和完善。
最后,很遗憾的是该书尚没有中文版(已经有法文、西班牙语版),因此我们也呼吁尽快把此书翻译为中文。
以下是著名美籍华裔哲学家成中英(Chung-ying Cheng)1969年写的述评(AGI翻译),发表于: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69, Vol.19 (4), p.455-457。
(YANG Xu WHU)
这是一本关于语言科学 (音系、音位学、词汇、语法、意义、语言分类、双语制和语言变化) 以及语言学如何与写作、生活和符号系统整体相关的优雅简洁 (包括索引在内的二百四十页) 但内容丰富的 (十二章七十二个主题) 的书。任何仔细阅读本书的人都会对许多语言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迅速深入了解语言学的各个方面。大量新颖巧妙的例子用于阐明作者的观点。本书还有一个新颖的特色:现代汉语和古典汉语都被作为例证引入。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作者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汉语语言学家,他在普通语言学和汉语教学以及普通话语法方面的贡献使汉语成为语言理论建构的重要试验场。
作者讨论了一些以各种方式被证明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例如,从赵教授对语言单位(例如音素和语素)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意义的区分必须预设为区分的标准。也就是说,不同的音素会在构成更大单位 - 语素 - 时在意义上产生差异,不同的语素是相对框架中具有不同意义的最小子单位。因此,语言学研究的形式基础显然无法与意义的考虑分开,这些意义不一定本质上是语言的,也未必在所有语言中都统一确定。这意味着如果不参考特定语言,就无法定义音素和语素。词的概念也一样。根据赵教授的说法,识别语言中的词语需要使用各种标准,例如自由和受限出现、通用性和受限出现、以及参考功能框架和停顿。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样的识别过程中,必须隐含地参考意义。现代汉语的“字”就是一个例子。“字”并不完全等同于印欧语系的“词”。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统一意义的体现,这种意义在其他语言中可能并不存在,并且可能在其他语言中被分解为多个词的显式成分意义。这表明词的概念定义必须针对特定语言进行,词义的分布应该被视为语言之间差异的问题。

赵教授不仅认识到词的性质在不同语言之间存在差异,而且还认识到形态学、句法以及它们在即时成分分析 (IC) 中的划分问题也因语言而异。这些差异体现在顺序、形态变化、语音修饰和形式类别成员等方面。它们也体现在生成结构方面,例如核心句和转换规则所表达的结构。在这方面,赵教授并不否认诺姆·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重要性。事实上,赵教授指出,句子或即时成分结构的意义通常由与其某种方式相关的规范 (核心) 结构决定。当然,这种决定必须相对于所讨论的每种具体语言。我们实际上可以将其称为语言中背景句子决定意义的原则。
赵教授认为意义可以纳入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他认为研究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比较具有相同意义的形态 (可以互换使用并被认作具有相同意义),二是将语言形式与事物的特征 (例如数字或亲属关系) 联系起来。总而言之,他认为语言形式的意义要么与世上的物体相关,要么与说话者对他人、言语指称对象或言语行为的态度相关。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从赵教授的观点来看,意义使我们能够指称事物和表达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意义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赵教授关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区分,以及指示意义和行为意义的区分,似乎为阐明上述观点提供了基础。
赵教授进一步指出,同义词和其他许多意义方面一样,也是程度问题。他没有给出原因,但我们可以推测部分原因在于,不同的同义词可能具有不同的背景句子和生成结构,作为其意义的母体决定因素。我们还可以指出,同义词与同音词或同形词之间的区别也可以视为程度问题。因为没有两个同义词的意义完全相同,每个同义词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类型,具有两个同音的实例或标记,每个实例或标记都具有不同的意义。赵教授也承认意义的差异以及语言形式的意义性都是程度问题。在研究语言形式的意义性问题上,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给定类型形式的多样性越大,每个形式的信息量或意义就越丰富。这当然可以解释为,非冗余形式越具体,其适用范围就越窄。
在总结我对赵教授关于意义问题及其影响的讨论的观察之前,我想指出的是,根据赵教授关于形态、句法和意义在个体语言中的相对确定性观点,他自然而然地得出了维特根斯坦式的结论,即意义和语言区分应该从语言在生活情境中的使用语境中学习,并且必须依靠这些语境来进行正确的语言分析。
赵教授清楚地论证了语言主要是口语,并且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语言可以被视为一套习惯,通过一系列不同风格的方言家族来展现。但是,通过同构和扩展的方式,可以在口语的基础上发明书面语言和其他形式的符号系统。正如赵教授所说:“同构在范式上与语言相同,扩展在句法上与语言相同”(第 122 页)。因此,根据赵教授的说法,符号系统是语言的一种概括,语言是符号系统的一个例子。
遵循皮尔士和莫里斯的观点,赵教授将符号视为一种易于产生且具有约定俗成(通常是任意)的与被象征事物之间关系的东西。同样,他也将符号与图标区分开来,并承认语言层次(例如符号的符号)是可能的。此外,他还列举了十个良好符号的要求,例如简洁、优雅、通用性等。他认识到这些需求经常会发生冲突,并且权重很难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基于不同语言并且相对于不同使用目的的概括。每个概念,例如简洁性,都必须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进行相对描述或定义,不能独立于语言系统之外。因此,在制定良好的符号系统时必须适应某种实用主义。
赵教授特别强调,翻译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语或双文本关系,而是一种三元关系,除了两种语言或两种文本之外,还涉及使用情境。因此,翻译不仅取决于翻译目的,还取决于翻译材料的类型。由于翻译需要建立等价标准,因此必须认识到存在许多等价标准以及制定这些标准的多种方法。正因为如此,赵教授指出,文本的直译和意译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翻译的构成要素方面通常可以存在整个连续的光谱,既可以直译,也可以意译。此外,由于意义有多个层面,因此翻译也需要应对多个语义忠实度维度。通常可以区分语义翻译和功能翻译,好的翻译既要保持语义相关性,也要保持功能相关性。
总而言之,我认为无论是语言学专家还是非专家,阅读赵教授的书都会受益匪浅。这本书也许还可以作为语言哲学等课程的语言科学简要入门读物。
创业/副业必备:
本站已持续更新1W+创业副业顶尖课程,涵盖多个领域。
点击查看详情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