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面蓝字“烟火丫头”请关注我吧

汝州的魔怔女人
著者:司卫平
一
你想朝前走一步,但紧张得半步都走不了。
在一树花开的桃树下,你脚穿着大红色虎头靴子,靠树干站着。大红虎头靴子用五颜六色的丝线绣出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的图案,踩在粉红色的瓣瓣落花上。
你的前面是蹲着的爹。爹嘴里喊着乖,眼神也在迫切地鼓励你,一双手朝你伸着示意,希望你抬起脚,走到他的怀抱里。爹爹的左边站着你的娘,娘弓着身子很焦灼,嘴里在告诉你,“抬脚,娇娇娃儿,你抬脚——”爹的右边和后面是你的花娘和几个婢子,没有一个人不是眉毛弯着,眼不错神儿地看着你的一举一动。
你最后还是胆怯的没有抬腿,哪怕是走出一小步,委屈得小嘴一撇,两只小手抹着泪“呜啊呜啊”哭了起来。爹探身把你揽在了怀,娘忙着给你擦泪。你的委屈更大,搂紧了爹的脖子,咿呀咿呀地哭诉着。其他的人也都围着你爹七嘴八舌地哄你,实际上像是在哄你爹。你躲在爹的怀里,哭得很羞怯。
你知道爹亲娘亲家里的人都亲,但你可能还不知道,你是这座被称为“洋楼院”的夏家宅邸里,十几年间生出的唯一的一个女公子。虽然是花娘生的,但依然金贵的不得了。你都两岁半了,可能是被娇惯的,也可能是天生胆小,不敢走路让大家焦急。不敢说你笨,都说你是娇贵了一双脚。
你奶奶安然地坐在上房的廊下,把金丝楠木的拐杖拄在胸前,很尊贵,很有威仪。你奶奶看着你爹的所作所为,只是笑呵呵地看着。这一阵子还是笑呵呵地看着你在人窝里泪眼纷飞,等你的聪明,等你的乖巧。你果然开始眼泪巴巴地看奶奶,粉嘟嘟的小手伸出来,朝着奶奶哭喊着张望。奶奶这时候才说话,很柔和,但音色圆润,“快把俺的小乖乖娃儿抱来。”
爹抱你走向廊下的奶奶身边。你的小手一直朝奶奶伸着,感动了奶奶,奶奶幸福的眼窝泪津津地。奶奶把拐杖递给婢子,接过你放到腿上,擦你脸上的泪痕,在你娇嫩的小脸上亲了几口。奶奶埋怨你爹说:“绕着俺的罗圈椅子都能转圈儿了,我叫一声‘芙蓉’,孩子会答应一声。你闲着没事吓孩子。知不知道,女娃儿,晚走一天添一分巧,晚一天挪步多一份娇贵。”
一群女眷们都附和着奶奶的话。奶奶十分爱怜地夸你说:“俺乖乖娃儿是细白细白的粉嫩,那咋就恁白呢。小脸粉红,咋看咋像是一个花骨朵呀!”
你娘有些自得地讨巧说:“娘是夸俺闺女嘞,还是夸您自己闺女嘞?老话不是说了嘛——侄女仿家姑,芙蓉还不是跟着采莲的细模样儿长的。”
奶奶逗着你笑得合不拢嘴。爹爹开始蹲下,给奶奶揉膝盖。你,对,你叫芙蓉,你的小手在爹的瓜皮小帽子上拍打。你闻惯了奶奶和娘头上的焗油气儿,这时候,爹爹头上散发的中药气儿十分地吸引你。奶奶把你的手收束住,你还要撑着。奶奶说你:“你爹的头不能摸。男人头、女人脚,光能看,不能摸。”
奶奶又说你爹:“祖德你站起来,不揉了。”
你爹说:“她才多大?她是恨我刚才逗她。”
奶奶笑着放开了你挣扎着的胳膊,宠爱地说:“拍吧,看你爹咋娇惯你!”
这时候,有一个婢子从跨院里走出来,脚下得很重,像是小跑。婢子直接走到你奶奶面前,仓促行了一礼,轻叫了一声:“老太太。”
你奶奶端起脸,轻声慢语地责备婢子说:“你是在采莲房里的,不是粗手大脚的使唤丫头,不能轻手轻脚的呀?啥事?”
婢子又是杀身一礼,勾着头小声地说:“小姐在房里哭。”
在场的人都听到了,都看老太太的脸。老太太惊讶地“嗯”了一声,问:“不是你陪着采莲看嫁妆嘛,是不是嫁妆不可心?说吧。”
婢子点着头,拘谨地瞟了一眼你爹,说:“是的,小姐看了两天嫁妆,左看右瞧,说少了一把砸核桃的木锤儿。”
老夫人看了看你爹,说:“我就知道,这后院里没有人能惹采莲哭。祖德,叫那些南蛮子匠人多做几个样式的砸核桃锤儿,采莲挑剩下的,各房里也放一把。”
你爹讪笑了一下说:“啥都没有忘,却就把俺妹子这点小嗜好给忘记了。我叫人去吩咐,赶紧点儿一后晌就能做出来。”
你爹要去前院,伸手把你从奶奶怀里要下来,要抱着一同去。他是一刻也不舍得离开你。奶奶说:“把芙蓉放下。小妮子家,由着你这样抱来抱去,长大了还能收在屋里。”
你爹满脸堆笑地说:“趁着小,叫闺女到处看看。”
你也坚持着,口里乍乍呼呼:“俺去俺去俺去——”
奶奶没有再坚持,对着身边的女眷们说:“祖德咋跟他爹一样儿,就喜欢闺女。看采莲惯成啥样儿了,就知道以后芙蓉能惯成啥样儿,一准比采莲还上脸。”
你爹抱着你,笑呵呵地边走边回奉娘说:“那才叫侄女仿家姑,是咱夏家的造化嘞。”
这一年,你像一个才挂蕾的花骨朵。娇小、柔嫩,一滴露珠就能淹没你的全部。你爹却看到你的含苞欲放或者花蕾初绽,他爱你像是爱眼珠子,一眼瞅不见你,就惶惶地,哪怕是坐着问诊,也要抽空跑回内院看你一眼。这时候的你总赖在哥哥身边背“汤头歌”,哥哥背你也背,虽然口舌不清,但你背的让爹稀罕。他对你奶奶说:“娘,芙蓉长大,比采莲还会出色。”
采莲拉着脸说你爹:“哥哥——夏祖德,再说俺的坏话不让你进堂屋。俺也不喊你哥哥。俺也不喊胭脂嫂子。”
胭脂是你娘的名字。
夏家不农不商,以行医立世,祖传几代外人说不清,但名声响几省却是真的。据说,夏家有两本祖传秘方,一本是传授家传验方的,一门里的子侄们,从小在在洋楼家中学医,长大了揣本祖传秘方去行医;而另一本是专门传授药材炮制的,只传长房长孙,不论子侄们行医的足迹遍及大河上下、还是大江南北,秘方里的药材必须还要长房长孙在夏家的老宅里炮制。如此一个家规,就使得夏家人有上百口,却不敢分锅灶;财源广进,归宗于长门。人们经常能看到,夏家的偏门里有蒙着黄油布的胶轱辘大马车出入,从洋楼过县出省去送药。
也是有了如此的家规,更让人咂舌的说法就流传开了:夏家的药铺子开的遍地都是,夏家人走府过县,远行千里不住二家店。
过去人提起富得不行不行的大户人家,喜欢用楼花雪片来形容。夏家,那可真是楼花雪片一般!
夏家上辈人传下来“分门另过不分家”习惯,人一辈多出一辈,房子就得一个院落一个院落的盖。盖房子的钱财都是从长门长房里出,长房里就只能不偏不向把房子盖成了一个一个的一模一样的院落。一个小家是一个院子,一支人合成个大宅院,一门人合成个洋楼寨子。
夏家的大宅院占据着半座寨子,宅院里也是有街有巷。在方圆几十里地的茅舍瓦屋里,就像鸡群里的凤凰。远处看,浑砖到顶的青砖院墙围着一大片浑砖到顶的楼房;近处看,青砖雕花、飞檐走兽的门楼阔大气派;进过这院子里的人都说,里面是一进院落套着一进院落,不是常年住在里面的人,谁进去谁迷。
老百姓眼窝浅,方圆几十里地的人,看个病不说是看病,都说是去“看洋楼”。看洋楼回来,张开嘴不是说“夏家的洋楼”,就是“洋楼夏家”,一会儿的见识能说成一个话题,一说几个月。
祖德是夏家这辈人里顶门立势的掌柜,也就是这一辈夏家后代里的长房长孙。不说他屁股下坐着个金山银山,只拿着那本祖传秘方,身份就主贵的不得了。
汝州的县长有病了,病怏怏地坐着洋车找上夏家门,求夏先儿能施以妙手。夏祖德当下给他把脉问诊下方子,临走连送出大门都没有,说是等的病人多。县长窝着一肚子火,出来门准备撒撒邪气,看见夏家门前的街道上排长队等着看病的老百姓,歪歪嘴乐了,说:“夏先儿还是很给面子啊!”
洛阳城里的吴佩孚得了病,不但身边的医生治不了,连西洋来的洋大夫也束手无策。咋办呢?只好开着漆黑锃亮的鳖盖车从西工兵营来找夏家。那吴佩孚是啥人,是直系军阀的总司令;一个中国都可以不听北洋政府的,但大半个中国都得听他吴佩孚的,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几个能尿出硬水的实力派人物。吴佩孚动动屁股,自然是前呼后拥的随扈众多。他的鳖盖车还没有开进洋楼街的寨门,整座寨子里里外外都站满了保护他的兵。兵们站得板正,脖儿梗子直溜溜地,脑瓜子动都不动。夏家当时也很紧张,一家子人吓得走路都是溜着墙根,不知道这吴佩孚是看病还是借钱。夏祖德硬着头皮站在自己的门楼上,抱拳给当兵的施礼。当兵的像木桩子,理都不理他。他知道怕也不是戏,就小跑着去后院给娘磕头。
他对娘说:“娘啊,兵匪不是土匪,光怕不中了。”
娘也怕,把采莲和几个孙子孙女收拢在自己的身边,拐杖横担在椅子扶手上,一屋子里挤满了家里的女眷。娘说:“自古至今,帝王都不叼咱医家的食儿,有了洋枪洋炮,这世道就没有规矩了?”
他怕吓着娘和一屋子的人,强装骨气地说:“俺就是来跟娘说一声。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人都不是铁打的,兴许是来找咱家看病呢!”他安抚了家里的内眷,吩咐几个精壮的相公,二门的内宅要上抬杠,拿几把枪守着。自己走到前面,把爹爹留下的拐杖找出来,学着娘的样子自己拄上,干脆就大开大门迎客了。
夏祖德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忐忑着站到大门外的台阶上,看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士兵,腿肚子直打哆嗦。当一辆乌黑锃亮的鳖盖车徐徐地滑到他身边的时候,上下牙都敲出了“咯咯”的声响。那车门开了,前车门下来的人瞟了一眼僵直的夏祖德,“嘭”地一声随手关上,很敏捷地同时拉开了后车门,恭敬地从后车门搀扶出一个人来。夏祖德偷着打量了一眼鳖盖车里钻出的人,悬着的心“扑通”就放下来了,擦拭着额头上浸出的细密的汗珠子,暗出一口长气,整个身子都舒缓了。他怕吴大帅来要钱要命,却不怕病人来求医呀!
夏祖德先曲身拱手给吴大帅施礼,然后前面先行引路。一群随扈前呼后拥地把吴大帅搀扶上台阶,涌进家里。待病怏怏的吴大帅在前堂坐定,夏祖德招招手让大帅的副官过来,慢条斯理地交代道:“留一个人照应大帅,其他人等都到寨外候着,杀气太重,不利治病。”吴大帅难受得这时候只想听大夫的话,点个头就准了。
夏祖德从吴大帅下车到进前堂,早观察了他的面相。见他两眼红肿,嘴角泛白,肚子一阵阵疼的双手捂着不松开,心里已经有了八分把握。把前堂的闲杂人等轰出去后,耷拉着眼皮给大帅把了一阵脉象,又托着大帅的下巴细细地审视了舌苔,声音平和地告诉大帅,是积食上火了。吴大帅也是著名的读书人,粗通医理,咧着嘴摇头不信。自己难受了许多时日,难道就得了这样的小病?
夏祖德安慰吴大帅道:“大帅是金贵人,没有把握,我哪敢贸然断言。听俺的话,下过药过一夜能去八分病。”他把吴大帅安排到客房,当下就亲自抓药熬汤,看着让其服下。
吴大帅喝下汤药,不到吃一碗饭的功夫,就觉得内里如百爪挠心,五脏如翻江倒海一般,烦躁得要死要活!这时候,夏祖德叫人拿进来一个茅桶,让副官伺候着强装骨气的吴大帅脱下裤子坐上去,不大一会就听到大帅的臭屁连连,拉稀拉得连头都直不起。
吴大帅在夏家的茅桶上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日露头,拉脱相的脸上已经露出了清气。他拉着夏祖德的手很虚弱地说:“夏先儿,我的病好了!”说完,闭上眼“呼呼”地睡着了。副官这时候才轻松地告诉夏祖德,大帅这病是跟总统闹别扭闹出来的,已经半个多月吃睡不下了。洛阳城里的大夫请个遍,药越吃,症越重,你是神医呀!
吴大帅住在夏家不想走,吃了睡,睡了吃,夏家的后花园也让他给转了好几遍。将养四、五天后,精气神都有了,才肯离去。临走的时候他告诉夏祖德:“很想叫你夏先儿随俺去,但张不开口呀,让你舍下这么大的家业,和让俺舍下那千军万马一样,都不容易!给你撇下一辆小轿车,权作延医之资吧。”夏祖德摆着手推辞,吴大帅拦住他的话头强调说:“随叫随到吧,常去洛阳看我。”
从此,夏家有了老汝州的第一辆鳖盖车。老汝州也都知道了这鳖盖车的来历。
那天,夏祖德本是去吩咐一下给妹妹做砸核桃锤的事,但出了二门就走不到前面了。他怀里抱着的芙蓉看到了二门外停放着的鳖盖车,着急的伸着手挣着身子,不哭不闹,只是含混不清对着夏祖德叫:“爹,坐车;爹,坐车,坐车——”她的表情很迫切,还用小手去扳着夏祖德的脸朝车那儿看。
别说是坐车,就是上天摘星星,娇宠着女儿的夏祖德也愿意去试试。他曾不止一次带着芙蓉坐在鳖盖车里出去玩,绕着寨墙转一圈再回来。芙蓉要是坐在车上不下来,那就一圈一圈地转。他喜欢看芙蓉笑颜如花的兴奋,看着心里就像抹了蜜糖般的甜,所以只要芙蓉有兴趣,他向来不会拒绝,一个慈父在女儿面前的软弱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实际是有着一个无法说出来的小心思,小妮子长到六、七岁上就该缠脚了,缠上小脚后的芙蓉就不能再出门了,要被关在深宅后院里一直到出嫁。每每想到这些,心都会突然地悸动,好像芙蓉的小脚上已然缠上了那撕心裂肺的的缠脚布。带小芙蓉出去看一次,就感到是多一次对自己满心愧疚的弥补,对自己负罪感的救赎。他曾对埋怨他的胭脂说:“在咱花骨朵一样的闺女面前,我的心软得就像是一颗熟透的柿子,情愿被她甜丝丝地吃掉!”
夏祖德抱着芙蓉往鳖盖车边走的时候,交代跟在身后的一个小相公说:“去交代匠人,快点做核桃锤,不一样的式样多做几把,后院里各屋都要使嘞。”得了话,小相公一溜烟就跑走了。
小相公跑到做家具的场院里,除了几个伙计在给家具上大漆,不见木匠大师傅的影子。一问才知道,大师傅去寨外的汤锅上喝茶去了,踅脚又往汤锅上找。寨外的汤锅上搭着几十领席子的大棚,棚子下面坐满了挑煤拉脚的人。那大师傅已经在夏家做了十几年活,经常坐在这汤锅上喝茶,跟这些挑煤拉脚的都成了熟人。都知道木匠大师傅是夏家专为做嫁妆从南方请来的,挑煤拉脚的人走四方,所以夏家为了嫁闺女都做了多少嫁妆,三五十里地的人都一清二楚。
这个小相公也是打小就在夏家的药柜上当学徒,年数多了,才被允许跟着夏先儿身边学能处。见着这么多人在,不由得就有了长大成人的显摆。他走到正兴高采烈地跟人摆龙门的大师傅身边,抢风头似地提着腔打断话头说:“大师傅,掌柜的叫你。”
大师傅扭头,撇这南蛮子腔问:“啥事?”
他有些幸灾乐祸地环顾着大家伙说:“掉底子事。”
大师傅纳闷了,担心是家具被掌柜的挑出了毛病,挠着头站起来就要走。
他拉住大师傅的胳膊说:“甭去应卯了,掌柜的叫我来传话,你给小姐少做了一个砸核桃锤儿,喝完汤快点做出来。”
大师傅听后,长出了一口气,说道:“吓我一跳啊,啥大的事嘛!连痒痒挠都做了,还就是没有想起砸核桃锤儿,眨眨眼的事儿。”
他有些托大地埋怨大师傅说:“那你眨眨眼啊。”
大师傅有些尴尬,说:“眨眨眼也得半个月吧,还得上大漆。”
面对着一群衣衫褴褛的穷汉们,俩人的对话很尖利,像是一把能刺穿神经的针,甩向了这个对富贵充满了敏感的人群,令人一下子就陷落在寂静的沮丧里。这样的气氛是多么地催人绝望啊!
小相公看着大师傅三下两下扒拉完碗里的汤水,两人絮絮叨叨说着砸核桃锤儿的事走了。所有挑煤拉脚的穷汉都没有用钦羡的目光去目送他们,而是不约而同地把眼收在汤碗里,喝汤声此起彼伏地响成一片。
也就是在这时候,鳖盖车那节奏紧凑的马达声从寨门里传出来,把穷汉们的眼睛从汤碗上吸引起来。所有人都木然地盯着寨门洞,看着漆黑锃亮、流线完美的鳖盖车稳稳当当地溜着地面一滑而出,虎雄雄地带起一路细碎的烟尘,从他们的不远处驰过。此时此刻,那一双双黯淡无光的眼神,就像一根根细弱的线,该要承受多大的折磨啊!
就在人们都灰塌塌地再次把脸照在汤碗上的时候,寂静的人窝里竟突然闹出动静,一个挑煤卖煤的小伙子莫名其妙地使起气来。大家伙木呆呆看着他伸长脖子干嚎了几声,激情地挑起自己满满的两箩头煤,大步奔走到寨壕边,惨然地笑着撒在了寨壕的河水里,而且连一根扁担、两个箩头也全扔了进去。他豪情地拍着空空的两手,吊着眼扫视了这群朝夕相处的穷汉,破着嗓子撂下一句话,“挑一辈子煤也是穷,啥时候能娶起夏家的闺女当媳妇?”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一大群挑煤下苦的穷汉子无不为他的举动而瞠目结舌。那一挑子煤和家什是什么?是养着一家人的营生和本钱啊!说扔就扔了,日子不想过了?大家呆愣愣地看着他一耸一耸的肩头在夸张的摆动着渐行渐远。
穷汉子们的乐观说来就来,不知道是谁惊叹着喊叫了一声:“呵呵,他还想娶夏家的闺女,呵呵呵,姚宝安,你舅子是得魔怔了吧?”
人群中的笑声渐渐地响起来,人们都喊叫着“姚宝安”这个名字,搜刮着自己所有能想起的刻薄话,奚落着那个远去的身影。

作者简介:
司伟平,又名司卫平(笔名),男,回族,生于1963年,国家二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洛阳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洛阳市长篇小说学会副会长。多年来,出版和发表作品700余万字。
喝茶读书听音乐,让烟火气把光阴熏香。掬一捧月光,采一瓶荧火,将每一滴生活的美好都落在文字里。吹落读书灯,浑身都是月。夜色下烟火气中的人,如水中鱼儿般自由在文字中敞荡,活出恣意的自我。
创业/副业必备:
本站已持续更新1W+创业副业顶尖课程,涵盖多个领域。
点击查看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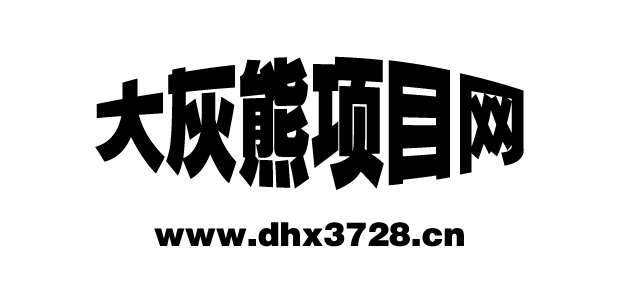

评论(0)